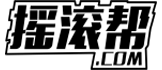不用乐器唱哭周迅的野孩子,是中国独立音乐人最好的榜样
8月1日,《乐队的夏天2》第3、4期节目播出,以Joyside为首的11支乐队进行了首轮竞演,而野孩子作为“乐夏2”资格最老的一支乐队,小组内最后一个出场,张佺、郭龙、马雪松、王国旭、武锐这五位来自西北的汉子,用黄河流淌千年的情怀熏陶出的深沉、古朴、深情,清唱了他们的代表作《黄河谣》。
这是来自心灵的激荡。
野孩子清唱完毕,现场观众沉浸在歌曲的情绪里,良久回不过神来。直到马东出来提醒打圆场:我发现结束了以后,居然没有人敢发出声音,因为生怕人家没完。
一旁的大乐迷周迅被感动得泪眼婆娑,她说野孩子的这首歌唤起了她内心唯一的一种情感,这个情感可能是关于家乡,也可能是关于父母。
最终,野孩子乐队得票167,位列小组第二,晋级下一轮。

这是乐夏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场无乐器演奏,纯人声清唱的作品呈现。
野孩子究竟是怎样由几位西北年轻人组建的小众乐队,进阶为如今这支被许许多多独立音乐人奉为榜样的传奇民谣乐队的呢?
一、相遇 1989年,还在上小学的张玮玮在去新华书店的路上,被几个穿着黑背心的家伙,抢走了他打算买三角板的两毛五分钱,后来他才知道,那伙欺负他的坏家伙们有个社团名叫“七小狼”,而这里面,有一个孩子叫郭龙。
也许是因为张玮玮太过于老实巴交,所以坏孩子郭龙三天两头地来找他要钱要烟,张玮玮每次不得不从他爸的烟盒里偷两根带给郭龙。 大概是因为总是被欺负吧,初一的时候,张玮玮学会了打架,还在中学里成立了个“十二锁链”社团,成员就是十二个常年被欺负的受气包,整天研究如何灭了“七小狼”。 张玮玮上了初二,被家人送去了西安上学。对于在白银出生的张玮玮来说,去趟兰州就算是进城了,而去西安,那就是进了省城。在西安,张玮玮接受了最早的摇滚乐熏陶。 在西安上了半年学,张玮玮又回到了白银,这次从西安回来可和以前不一样了,张玮玮成了一名街头吉他青年,他总是在后院支个铁丝床,点上柴油灯,聚集起一群人喝酒唱歌。郭龙也来凑热闹,时间一长,俩人便熟识了,郭龙这才发现,这个以前老实巴交的受气包,不光会识谱,还会弹钢琴和吉他。 1990年,14岁的张玮玮拜比他大1岁的郭龙为大哥,俩人跟着一个蹲过监狱、吉他水平超群的“队长”一起学吉他。 当时张玮玮住的家属院儿和郭龙家就隔着一堵墙,翻过那堵墙,直线距离不超过200米。据张玮玮自己回忆,他经常跳过那堵墙去找郭龙玩,有一次不小心还压塌了墙下摆着的砖。 和两个常常旷课、整天无所事事的问题少年不同,1968年出生于甘肃兰州农村的张佺,已经在青海做长途汽车的售票员了。 张佺在青海长大,后来又去过成都和杭州,他不但做过汽车售票员还当过油漆工,也曾经在四川、西藏、广东等地的夜总会和歌舞厅里当过乐手,给歌手们伴奏。 看过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用最自然的歌声表达着生活的忧伤和快乐的张佺,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做自己想做的音乐。 1995年2月,张佺结识了同样热爱音乐的索文俊小索,并在杭州成立了野孩子乐队。俩人蹲在西湖边,写下了《黄河谣》。而另一首传唱度颇高的赵牧阳的《黄河谣》,野孩子也曾经翻唱过,但改了名字叫《早知道》。
张佺在青海长大,后来又去过成都和杭州,他不但做过汽车售票员还当过油漆工,也曾经在四川、西藏、广东等地的夜总会和歌舞厅里当过乐手,给歌手们伴奏。 看过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用最自然的歌声表达着生活的忧伤和快乐的张佺,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做自己想做的音乐。 1995年2月,张佺结识了同样热爱音乐的索文俊小索,并在杭州成立了野孩子乐队。俩人蹲在西湖边,写下了《黄河谣》。而另一首传唱度颇高的赵牧阳的《黄河谣》,野孩子也曾经翻唱过,但改了名字叫《早知道》。 3个月后,他们返回了大西北,沿着陕西和山西境内的黄河徒步一个月采风,并花了一年的时间,倾听了农民和牧人的信天游、花儿和秦腔,并借鉴了这些音乐语言,汇成了野孩子独特的音乐风格。 1996年3月,张佺和小索来到北京发展,认识了一些乐手,并于1997年1月1日,在大西俱乐部,开始了野孩子乐队的第一场演出。 1997年3月,张玮玮从成人委培的师范学校毕业,他父母商量着给他找个工作,要么去私立小学当老师,要么花点钱去交警文工团。家里人又借钱又送礼,让张玮玮觉得难受,所以他拉上郭龙逃到了广州。
3个月后,他们返回了大西北,沿着陕西和山西境内的黄河徒步一个月采风,并花了一年的时间,倾听了农民和牧人的信天游、花儿和秦腔,并借鉴了这些音乐语言,汇成了野孩子独特的音乐风格。 1996年3月,张佺和小索来到北京发展,认识了一些乐手,并于1997年1月1日,在大西俱乐部,开始了野孩子乐队的第一场演出。 1997年3月,张玮玮从成人委培的师范学校毕业,他父母商量着给他找个工作,要么去私立小学当老师,要么花点钱去交警文工团。家里人又借钱又送礼,让张玮玮觉得难受,所以他拉上郭龙逃到了广州。
两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在天河体育中心的地下通道里、在人声鼎沸的大排档里卖唱,每天挣来的钱还不够果腹,俩人差点饿死,最后和郭龙两三天没吃饭,凑钱买了一张到西安的火车票,买不到兰州。火车开出广州的时候,张玮玮都快哭了,他说:将来广州市市长抬着轿子到兰州来接我,我也再不来了。 二、榜样 1997年7月,回到白银的两位无业游民,整天泡在一个贝斯手开的酒吧里,因为当时很多原创乐队都去他那演出。但他俩实在太穷了,整天蹭演出看却消费不起酒吧里的酒,于是好心的酒吧老板留下了他们做店里的服务员。 俩人很开心,这样不但能赚一份工资,还能每天看免费的演出。 那个时候已经小有名气的野孩子,正好来到张玮玮和郭龙打工的这间酒吧里演出。当时传说野孩子的风格,是用重金属唱甘肃“花儿”,张玮玮和郭龙对这支乐队相当感兴趣。 在张玮玮的印象里,玩摇滚的尤其是玩重金属的,一定是皮夹克、长头发、牛仔靴、带耳环,演出时台下一定会有姑娘的尖叫。但野孩子演出的时候,张玮玮和郭龙却看傻了,因为这俩人和他们印象中完全不一样。张佺和小索两个光头,穿着灰色T恤衫和黑裤子,他们站的直直的,眼睛亮亮的。 张佺拿起了用布包裹起来的吉他,说:这首歌献给真正听音乐的人。然后用木吉他弹起了西北民谣的旋律,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来时,张玮玮和郭龙就被震惊了。
在张玮玮的印象里,玩摇滚的尤其是玩重金属的,一定是皮夹克、长头发、牛仔靴、带耳环,演出时台下一定会有姑娘的尖叫。但野孩子演出的时候,张玮玮和郭龙却看傻了,因为这俩人和他们印象中完全不一样。张佺和小索两个光头,穿着灰色T恤衫和黑裤子,他们站的直直的,眼睛亮亮的。 张佺拿起了用布包裹起来的吉他,说:这首歌献给真正听音乐的人。然后用木吉他弹起了西北民谣的旋律,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来时,张玮玮和郭龙就被震惊了。
张玮玮说,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乐队是可以很“正”的。而且,在生活中到处都能听到的“花儿”,没想到是那么的有音乐价值。 从那时起,21岁的张玮玮就拿野孩子当做了人生和音乐的榜样,并且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变过。 那场演出过后,张玮玮决定追随野孩子的步伐去北京发展。但郭龙却觉得北京太远了,况且俩人在广州都混不下去,去北京会更难。 于是,26天后,1998年7月26日,张玮玮一个人坐上了火车,来到了他向往的北京。 张玮玮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野孩子。野孩子那个时候住在中国歌舞团,何勇住三楼,野孩子住楼下的地下室。 与凉爽的兰州不同,北京太炎热了,刚来北京的张玮玮特别不习惯,但野孩子住的地下室凉快,于是张玮玮没事就去他们的地下室,一是蹭凉,二是偷艺。 很快,张玮玮在琴行找了个工作。在琴行工作可能是当时的北京摇滚青年的最佳出路了,不但能弹琴,工作还清闲。没过多久,张玮玮给郭龙打了个电话,他说:来北京吧,来琴行上班,周围一条街全是高手,特别牛逼。 于是郭龙也来了,但待了不到一年,还是回了白银,因为他实在不喜欢上班的生活。 张玮玮在琴行待了两年多,白天上班,晚上去酒吧唱歌挣钱,还带了几个学吉他的小徒弟,收入不低。 2000年初,张玮玮跟琴行里的一个人打了一架,连工资也没拿,就辞了职。他搬到了小索家隔壁,小索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小索起床,他也起床,小索练琴,他也练琴。晚上,再到小索家蹭个饭,衣服脏了,小索给他洗。 张玮玮一直都很想加入野孩子,但一直没有机会。直到有一天,张佺对张玮玮说,乐队想扩大,问他会不会键盘,张玮玮说会,又问他,手风琴会吗,张玮玮还说会。 其实那个时候,张玮玮已经很久没有碰过手风琴了,张佺问过他之后,他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让他把那架星海手风琴从白银寄去北京。手风琴到了的那天,张玮玮一晚上没睡,把那首歌练了两天一夜,才加入到了野孩子。那首歌就是现在他们的开场曲《死之舞》。
与凉爽的兰州不同,北京太炎热了,刚来北京的张玮玮特别不习惯,但野孩子住的地下室凉快,于是张玮玮没事就去他们的地下室,一是蹭凉,二是偷艺。 很快,张玮玮在琴行找了个工作。在琴行工作可能是当时的北京摇滚青年的最佳出路了,不但能弹琴,工作还清闲。没过多久,张玮玮给郭龙打了个电话,他说:来北京吧,来琴行上班,周围一条街全是高手,特别牛逼。 于是郭龙也来了,但待了不到一年,还是回了白银,因为他实在不喜欢上班的生活。 张玮玮在琴行待了两年多,白天上班,晚上去酒吧唱歌挣钱,还带了几个学吉他的小徒弟,收入不低。 2000年初,张玮玮跟琴行里的一个人打了一架,连工资也没拿,就辞了职。他搬到了小索家隔壁,小索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小索起床,他也起床,小索练琴,他也练琴。晚上,再到小索家蹭个饭,衣服脏了,小索给他洗。 张玮玮一直都很想加入野孩子,但一直没有机会。直到有一天,张佺对张玮玮说,乐队想扩大,问他会不会键盘,张玮玮说会,又问他,手风琴会吗,张玮玮还说会。 其实那个时候,张玮玮已经很久没有碰过手风琴了,张佺问过他之后,他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让他把那架星海手风琴从白银寄去北京。手风琴到了的那天,张玮玮一晚上没睡,把那首歌练了两天一夜,才加入到了野孩子。那首歌就是现在他们的开场曲《死之舞》。
野孩子的生活特别规律,早上几点起床、几点练声、几点练琴、几点睡午觉,全都是有规矩的,张玮玮开始按照野孩子的规矩,加入了排练。 80年代是一个信仰真空的年代,那个时代,过去已经过去了,但新的还没到了,所以年轻人很痛苦,因为没有任何方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些什么才有意义,喝酒也没意思,打架也没意思,但找不到一个发泄的出口。 张玮玮碰到了野孩子,才突然知道,人就应该这么活着,才算是没有白活。 在北京一稳定下来,张玮玮就给郭龙打了个电话,他说这回是真的牛逼了,你快来。于是郭龙也来到了北京,加入了野孩子。
郭龙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觉得一个人每天早上八点准时起床练琴,那这人肯定是傻叉,但等到他二十多岁,才发现只有真正牛逼的人,才能坚持住这样的生活。 张玮玮和郭龙两个“坏孩子”,开始和野孩子一样,每天锻炼身体、练琴唱歌,并且学着对周围的人善良。 2001年,小索提议开间酒吧,一是为了维持生计,二是乐队也能有个排练和演出的地方,于是,几个年轻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河酒吧。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野孩子自己盖的,墙上的砖是他们亲自去香山拉回来的,油漆都是自己刷的。 2002年刚过完春节,河酒吧就在三里屯南街正式开业了。 河酒吧很小,演出台也不大,野孩子固定每周五演出,周三由万晓利、小河演。随后,废墟、木马、舌头、都曾经去那里演出,河酒吧变成了音乐爱好者们的聚集地。李修贤、杜可风、罗永浩这些人没事也会来坐一会儿。 从那以后,野孩子的排练时间改为每天下午两点,排练到四点,四点到四点半休息。休息的时候,乐队的人就挨个做俯卧撑,每人一组,一组60个。张玮玮说,这段时间,是他这辈子过得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河酒吧很小,演出台也不大,野孩子固定每周五演出,周三由万晓利、小河演。随后,废墟、木马、舌头、都曾经去那里演出,河酒吧变成了音乐爱好者们的聚集地。李修贤、杜可风、罗永浩这些人没事也会来坐一会儿。 从那以后,野孩子的排练时间改为每天下午两点,排练到四点,四点到四点半休息。休息的时候,乐队的人就挨个做俯卧撑,每人一组,一组60个。张玮玮说,这段时间,是他这辈子过得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河酒吧越来越出名,从十点钟开始,酒吧里就挤满了人,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过了12点全部都成为了朋友,小索经常过了凌晨一点就开始“开仓放粮”,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喝酒,直接去吧台拿,不用付钱。那会那群老的摇滚乐队,没有几个人没喝过小索请的酒,喝醉了就直接去小索家住。 也是这个时候,他们认识了一个叫安娜的法国姑娘,这位业余摄影师,拍下了2002年至2004年间,野孩子、万晓利、小河等地下音乐人的真实生活。这位叫安娜的姑娘,现在成为了演员刘烨的妻子,诺一、霓娜的妈妈。
河酒吧越来越出名,从十点钟开始,酒吧里就挤满了人,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过了12点全部都成为了朋友,小索经常过了凌晨一点就开始“开仓放粮”,所有人都可以免费喝酒,直接去吧台拿,不用付钱。那会那群老的摇滚乐队,没有几个人没喝过小索请的酒,喝醉了就直接去小索家住。 也是这个时候,他们认识了一个叫安娜的法国姑娘,这位业余摄影师,拍下了2002年至2004年间,野孩子、万晓利、小河等地下音乐人的真实生活。这位叫安娜的姑娘,现在成为了演员刘烨的妻子,诺一、霓娜的妈妈。
2002年的夏天,是个疯狂的夏天,诗人伊丽川将他们推荐给了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于是,《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这张充满了酒吧气氛的专辑问世了。 三、解散 2003年,北京闹起了非典,北京的酒吧陆续的关门了,河酒吧也停业了。非典过后,后海仿佛一夜之间,开起了十几间酒吧,三里屯南街没人去了。张佺和小索决定解散乐队,酒吧也不做了。 2003年5月,野孩子宣布解散。乐队解散后,张玮玮的心里落差特别大,他去了新疆,又到了伊犁,然后去喀什,又回到伊犁。张玮玮说他那几年过得特别黑,感觉没有了劲头。 2004年,张佺和小索去英国演出,演出时小索突然胃疼,三个月后,2004年10月30日10时20分,因胃癌晚期于北京协和医院去世。
小索的去世,对张佺影响特别大,张佺一个人背着冬不拉,从兰州出发去西藏,从西藏又到云南,他在路上写下了“北风抽打在身体和心上,远行吧远行。” 小索去世后,张佺对张玮玮和郭龙说,小索不在了,野孩子以后就靠你俩了。
张玮玮和郭龙俩人,似乎成为了野孩子的“遗孤”,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那些年,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从那以后,每年纪念小索,俩人都会唱《黄河谣》,并说自己以后的每场演出,都要唱一次《黄河谣》。 张玮玮为了纪念小索,还写了一首《石头房子》。小索埋到了兰州边上的一个叫卧龙岗的山上,他的墓地是用石头做成的小房子,所以张玮玮才为小索写下了这首《石头房子》。 2007年,张玮玮认识了一个姑娘,并在爱情的刺激下,写出了《米店》这首歌,因为这个姑娘的梦想是毕业后开一间杂货铺,而米店,就是她给自己的店起的名字,这个姑娘就是张玮玮现在的妻子。而这首歌,后来被一位南京的未知艺术家翻唱,被广大听众所熟知。 四、重组 2009年,张玮玮和郭龙来丽江演出,和张佺重新相遇,那个时候的两人,已经不是队友,而变成了两个独立歌手。 张佺在束河租了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种了一颗苹果树、一颗梨树。两人坐在院子里相对喝着茶,几年没见,各自早已有了其他的圈子,气氛有些尴尬。直到参观张佺家的时候,张玮玮才发现,二楼的楼梯墙上,贴满了野孩子当年演出的照片。 张玮玮鼻子一酸,他知道,张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记挂着大家的。年轻时候的情感突然被唤起,张玮玮虽然回到北京,但还是想和西北的兄弟们在一起。 2010年,张佺到北京演出,张玮玮和郭龙给他当嘉宾,这是他们自2003年解散后,第一次一起演野孩子的歌。 2011年10月31日,野孩子乐队重组,成员是张佺、张玮玮、郭龙。随后2013年,吉他手马雪松加入,2014年,鼓手武锐加入。
张佺在束河租了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种了一颗苹果树、一颗梨树。两人坐在院子里相对喝着茶,几年没见,各自早已有了其他的圈子,气氛有些尴尬。直到参观张佺家的时候,张玮玮才发现,二楼的楼梯墙上,贴满了野孩子当年演出的照片。 张玮玮鼻子一酸,他知道,张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记挂着大家的。年轻时候的情感突然被唤起,张玮玮虽然回到北京,但还是想和西北的兄弟们在一起。 2010年,张佺到北京演出,张玮玮和郭龙给他当嘉宾,这是他们自2003年解散后,第一次一起演野孩子的歌。 2011年10月31日,野孩子乐队重组,成员是张佺、张玮玮、郭龙。随后2013年,吉他手马雪松加入,2014年,鼓手武锐加入。
2013年,张玮玮和郭龙,把北京的房子退掉,收拾东西彻底搬到了云南,和兄弟们团聚。在云南,野孩子每周排练六天,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在排练休息的时候,野孩子把年轻时候做俯卧撑的这项运动,改成了踢毽子。 经过了风雨,野孩子开始尝试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乐队中的每一个都开始为乐队创作。张佺的《不要拿走它》,马雪松的《鲜花只为自己开》,野孩子变得开放。 2015年,野孩子在北京工体举办了二十周年音乐会,音乐会上,那些河酒吧曾经的朋友全都去了,仿佛一切都像13年前一样。 2018年,野孩子有了自己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大桥下面》。
2018年,张玮玮在他42岁生日那天宣布隐退,并暂停所有的演出及相关工作,并专心打理自己的个人公众号“白银饭店”。 2020年7月,乐队的夏天2开播,张佺带领野孩子乐队,清唱起了1995年张佺和小索一起蹲在西湖边写的那首《黄河谣》。野孩子的歌声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流进了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注1:本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注1:本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注2: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来源:MOGO《野孩子的故事 张玮玮 郭龙 专访》、一条纪录片《野孩子》